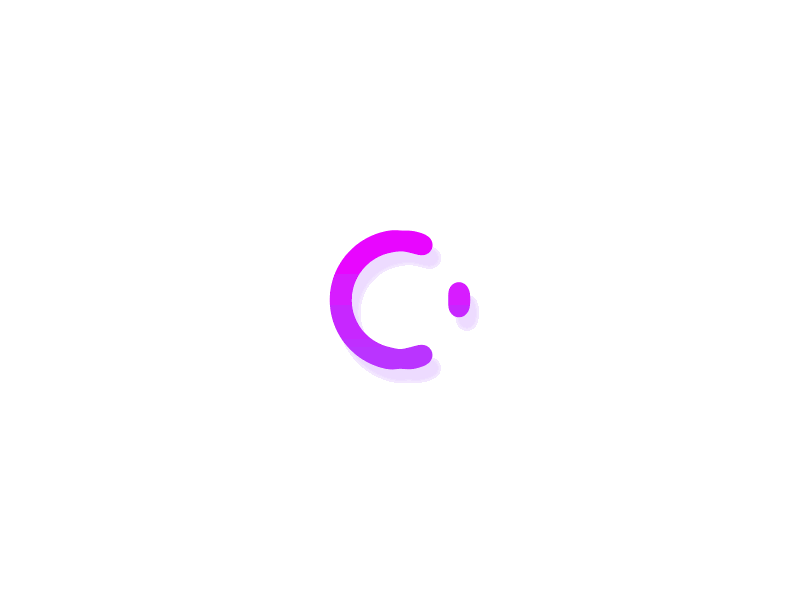
播放列表
正序
内容简介
傅城予接过他手中的平板电脑,却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让自己的精力重新集中,回复了那封邮件。 可是演讲结束之后,她没有立刻回寝室,而是在礼堂附近徘徊了许久。 见她这样的反应,傅城予不由得叹息了一声,道:我有这么可怕吗?刚才就是逗逗你,你怎么还这么紧张?我又不是你们学校的老师,向我提问既不会被反问,也不会被骂,更不会被挂科。 他的彷徨挣扎,他的犹豫踟蹰,于他自己而言,不过一阵心绪波动。 他写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件事,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,可是看到他说自己愚蠢,说自己不堪,看到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,她控制不住地又恍惚了起来。 这天傍晚,她第一次和傅城予单独两个人在一起吃了晚饭。